在如火如荼的光谷建设之中,有条道路绿化的问题,却成了光谷建设的难题。在当年(大约在2006年),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相关领导,召集了所有服务于光谷的园林企业和设计机构,公开征询“汤逊湖北路”的绿化问题。这条道路的绿化,经过了几轮施工、尝试了多种方法都不尽人意。因为,此路段两旁的绿化用地,基本是由建筑垃圾堆积而成,无论种植何种苗木,好像在这里都会水土不服。
我们踏勘现场之后发现,之前列植的广玉兰、桂花和樟树等苗木的长势,的确是惨不忍睹,要么成片的死亡;要么就是一副要死不活的模样,呈现出一派荒芜的景象。尽管如此,这里却并非寸草不生,在高低错落、起伏不平的复杂地形里,到处都长满了芦苇和芒草、并盛开着各种叫不出名字的野草和野花。
征询会上,在听完了各路专家的各种改善植物立地条件的建议之后,我提出的“要把汤逊湖北路建成'繁花似锦,彩蝶飞舞'之景象”的建议,深得东湖高新领导的赞同,并当即责成我们可按设想实践。也就是说,我的一个建议,凭空就获得了一项工程。
我向开发区领导陈述:你们现在就可以把“汤北路”所有值钱的苗木全部移走,不然,最终“汤北路”上所有的花草树木,都被算作是我们的重新营造。因为,我们要开启自然的自组织力,让自然的能动性参与到我们的景观营造之中。开发区领导非常赞同我们“化腐朽为神奇”的设想,并口头答应,我们要把原生植物当成景观来算工作量的想法。
在具体实施中,我们尊重现状,优先制定出要保护的东西,大量保留了包含芦苇在内的野草、野花。除了保留下来的原生植被,我们还根据地形适当引种了一些多年生的球根、宿根花卉,并构建出呈现自然形态的植物群落;在渠化岛和人行道旁等一些人工痕迹较强的地段,适当点缀了一些色叶灌木作为色块。我们摒弃了列植高大乔木的习惯做法,以丰沛低矮的植物、稠密艳丽的芳草,充分展现出此路段的独有特色。总之,“汤北路”所呈现出的景观效果,在当时,是一条与人们习惯认知很不一样的道路景观。

这是汤北路当年的景观效果,在当时的武汉,还造成了一定的波澜,它是武汉第一个具有“花境”概念的景观。
尽管我们在这里种植的球根、宿根花卉所营造出的植物群落,与现在城市常见的“花境”概念并不相同,但“汤北路”的建设,给武汉的城市绿化还是带来了些许变化:人们开始更欣赏植物群落之间的物种关系,而不是只关注单一树木的挺拔和秀丽。“汤北路”竣工后,不少参观过的市民惊叹:原来野花、野草也能如此美丽!在“汤北路”的示范作用下,我们发现在武汉的某些重要路段,还特意种植芦苇作为观赏植物,这样的做法,显然并不适宜,东施效颦必然适得其反。要知道,我们在“汤北路”把芦苇作为审美对象,并非是引种而来,只是把它本来就具有的美丽,用种新的方式展现出来而已。倘若,在一个不易生长或没有生长过芦苇的地方,硬性要栽种芦苇,这必将是个“吃力不讨好”的作为!
当然,刻意去种植野花、野草,而不是悉心去保留原生植物,这看似愚蠢的作为,也许在当下的基建环境下,也是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。其实,在“汤北路”的施工过程中,我们也不得已铲除了一些原本长势很好的原生植被,改种了一些常见的色叶灌木。因为,虽然这些原生的植被已经参与到整体的景观之中,虽然当初领导也同意,保留的原生植物能算作工作量,但是决算时,却找不到任何一条政策能够支持这样的承诺,因为野花、野草没有任何的采购、栽种等记录。所以,最终我们也不得不做出一些违心的事情去平衡财务。
尽管如此,“汤北路”的设计理念与普通花境的营造,还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。我们更强调原生植被在环境中的作用,人的主观意愿嵌套于自然的结构之中,这样,创造的生态价值,能够事半功倍。而花境,是人工刻意创造的植物群落,是自以为是的东西,虽然看上去好看,但并不一定能契合场所的特征,可以这么说,花境就是城市景观的奢侈产品,因为它需要更大的养管力度做支撑。
城市的道路绿化,不能只是作为一种审美对象来考虑,要把城市的整个道路系统以及城市的公共绿地,当作城市的绿色基础设施来打造。所以,面对每一项园林景观工程,我们都应该集经济、生态、美学来统筹设计。
1,景观的生态化设计不是创造奢侈产品,而是人类必须要做的行动。
上世纪60年代,美国科普作家蕾切尔·卡逊所著的《寂静的春天》把人们从工业时代的富足梦想中唤醒。蕾切尔·卡逊向人们揭示了,人类不断想要控制自然的结果,却使自然生态破坏殆尽,这不仅危害人类自身,甚至还遗祸子孙。从此之后,“生态和可持续”就成为人类各个阶层竞相使用的高频词汇,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已经成为当今人类发展的主题。
在什么东西都喜欢冠以“生态”名称的当今时代,越是叫得响的东西,越是容易让词义空心化。生态,或者说景观的生态化设计,现已成为人们说得最多,但又思考最少的东西。生态设计,其实不是某个职业或学科独有的称谓,它实际是一种与自然相互作用和相互协调的方式。其范围十分广阔,包含在当今的所有职业之中。生态设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框架,它帮助我们重新审视景观、乡村、城市、建筑等设计,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和行为。
生态设计是对自然过程的有效适应和结合,它需要对设计结果给环境带来的冲击进行全面的衡量,也就是说,针对每项设计我们都要认真去判断:它是有利于改善或恢复生命系统?还是破坏了这个环境;它是保护了相关的自然结构和自然的演化过程?还是在破坏它们?
带着这样的疑问,我们不妨来看看城市中那些看似花草繁茂的花境,这些刻意营造出的奇花异草,表面上的生机盎然,却需要持续的人工干预才能保持,其生态功能是需要代价的。如果城市中这类景观越多,城市的生态包袱反而越沉重。
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上面提到的“汤北路”,它正是一种以发现为基础的设计!大量的野花、野草,大多都是本地原来就有的物种,我们能让这里的景观大放异彩,只是对本身环境进行了一定的梳理,并不是主观的凭空创造,对自然原有的结构是种保护和修复。尽管,有人也抱怨“汤北路”养护太难,他们说:这哪里是养护,这简直是开荒!
其实“汤北路”在设计之初,并没有大量养护的计划,只是,那些原生的和新植的宿根、球根花卉在盛开时过于艳丽,以至于人们不忍心看到它们的凋落,人们把衰败的现象当作了废弃物,偏要彻底清除而后快。
2,自然界生生不息,没有废弃之物。
自然界没有任何的废弃之物,每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,都有一套完整的食物链和营养级。

营养级是指生物在食物链中的位置。在整个生物圈中,有一个能量传递的过程:绿色植物吸收太阳能,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和土壤中的微量元素固定下来,形成最基础的生物质,这是将无机物转化为有机物最基础的环节,所以,绿色植物又被称为“生产者”;然后,草食性动物,吃掉这些生物,生成蛋白质,它们被称为“初级消费者”;而肉食性动物,又将草食性动物吃掉,它们就叫做“次级消费者”;动植物的死亡,又被细菌所分解,重新变回肥料以供生产者进行再生产,这些菌类生物就被称为“分解者”。
在健康的生态系统里面,生产者,消费者,还原者是一个无限循环的闭环。秋天的枯枝败叶是春天新生命生长的营养,如果我们清除公园和城市公共绿地中枯枝败叶,实际上是在切断自然界的闭合循环系统。人类总习惯用人类自定的标准,来衡量物种的好坏。例如,好看或可食用的物种,就被定义为有用或有益,否则就是废物或有害。其实,即使按照人类自定的标准去判断,因人的认知局限,也不能一次就能断定什么是有益或有害,比如,过去人们普遍觉得狼是个有害的物种,因为它们伤害人畜,所以对待恶狼,除恶务尽就成为人们的共识;可是,在狼的数量越来越少的今天,人们又慢慢发现:狼是草原的保护神!
废物和垃圾,其实是现代文明的产物,大自然中是没有任何垃圾和废物的,一切都能循环利用,万物都可各得其所。正所谓:物无美恶,过则为灾。
3,自然的自组织和能动性
自然是具有自组织或自我设计的能力的。一个自然形成的水池,如果没有人工干预,不久后在其水中、岸边就会生长出许多昆虫、水藻、杂草等,最终会演化出一个物种丰富的水生生物群落。自然系统的丰富性,远远超过人为的能力。如其这样,我们不如开启自然的自组织或自我设计过程。

在踏勘了汤逊湖北路的现场之后,我们就本着要开启自然的自组织能力,让自然参与到我们的设计之中。既然基地环境是由建筑垃圾堆积而成,这就说明,此处的基础土壤是不行的。面对基础土壤不行的问题,常用的方法有两种,一是置换新土;另一种就是就地改良。置换新土,虽然立竿见影,但这只是一种转嫁矛盾的方法,即使我们找得到新土,但处理垃圾又成为另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。其实,处理垃圾在当今已成为影响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,所以我们在“汤北路”,采用的是,就地改良基础土壤的方法。
要鼓励自然的能动性,让自然参与设计,建立一个自律循环的自发秩序,我们就一定要克制尽量放下一双闲不住的手,要能够守得住一定的边界,并保持持续不断的进化推力,然后加上足够的耐心。自然的自组织和自我设计,有时当然会与人的预先判断不一致,比如,我们喜欢的花朵仍然会凋落;我们不喜欢的野草却不停在疯长。大自然不会因为我们的喜好而改变,如果我们以自己的喜好去干预自然,这就选择了一条与自然抗衡的路,与自然抗衡就永无胜利之日,我们就会觉得“汤北路”的养护会十分艰难。
上面我们说到,景观的生态化设计是人类的必须行动,这主要是指,人类在与自然抗衡的过程中,已致使自然的生态系统破坏殆尽,如果人类再不反省自己的过错,人类就再无繁荣可言。我们提倡景观设计,既要戒除工业造物的想法,又要戒除“种瓜得瓜”的小农意识。也就是说,设计要顺从自然的意愿,而不能与自然抗衡。所谓的小农意识,是指不管自然本身是否更适合生长大豆,我们都一味要追求瓜果,并不惜选择与自然抗衡。其实,瓜和豆都是农作物,如果我们适当改变一下欲求对象,立刻就能事半功倍!同理,鲜花与野草都能固碳释氧,我们何苦要如此憎恨野草?
尽管在天地俱生,万物以荣的春季,“汤北路”似乎更加迷人,但花朵的衰败和野草的疯长,也应该是设计本身的过程。“汤北路”设计之初并没有追求一成不变,变化也是“汤北路”的特色。我们不要大惊小怪某些鲜花被疯长的野草所淹没,这说明,此地段更适合种植这种野草,我们需要做的,其实就是尽量让野草也变得美丽!
英国著名博物学家、进化论的倡导者托马斯·亨利·赫胥黎曾这样描述过,一个人工花园,在无人照料时,便会被当地的杂草侵入,最终将人工种植的园艺和花卉全部淘汰。汤逊湖北路的景观营造,尽管不是一个纯粹的人工花园,但是,某些从温室引种而来的花卉,被生长能力更强的野花、野草所淘汰,这本来就是十分正常的现象,我们完全可以顺从自然的意愿,不断调整我们的预期,只要是芳草稠密,彩蝶在飞舞,又何必在乎它盛开的到底是什么花呢?
在什么东西都生产过剩的年代,曾经有一个产品却一物难求,这就是褚橙。同样是橙子,褚橙为何一橙难求,每年能够销售万吨,年产值过亿,而且价格比一般橙子要贵三倍?这当然与“褚时健15岁父亲去世;30岁把濒临倒闭的糖厂扶持起来;50多岁把亏损的卷烟厂做到亚洲第一,成为中国烟草大王;71岁成阶下囚,74岁高龄再次创业,连马云和王石都是他的小迷弟。”这些内容分不开。
但我想说的并不是这些,尽管褚时健的褚橙并不一定是口感最好的,但可以肯定的是,这个橙子的味道一定不是最差的。要知道,褚时健承包的哀牢山原来并不盛产橙子,褚时健是通过种草和种植其他植物,采用轮种的方法,从根本改变了植物的立地条件,做的是生态增量,不是简单的价值传递而是一种价值创造。
如果当年人们对待“汤北路”能像褚时健一样更有耐心,我们的城市园林景观的建设,做的就不会只是一种价值传递的工作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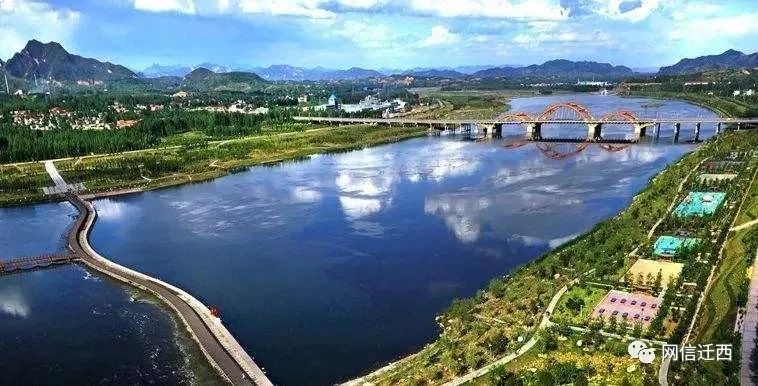







 加载中,请稍侯......
加载中,请稍侯......
精彩评论